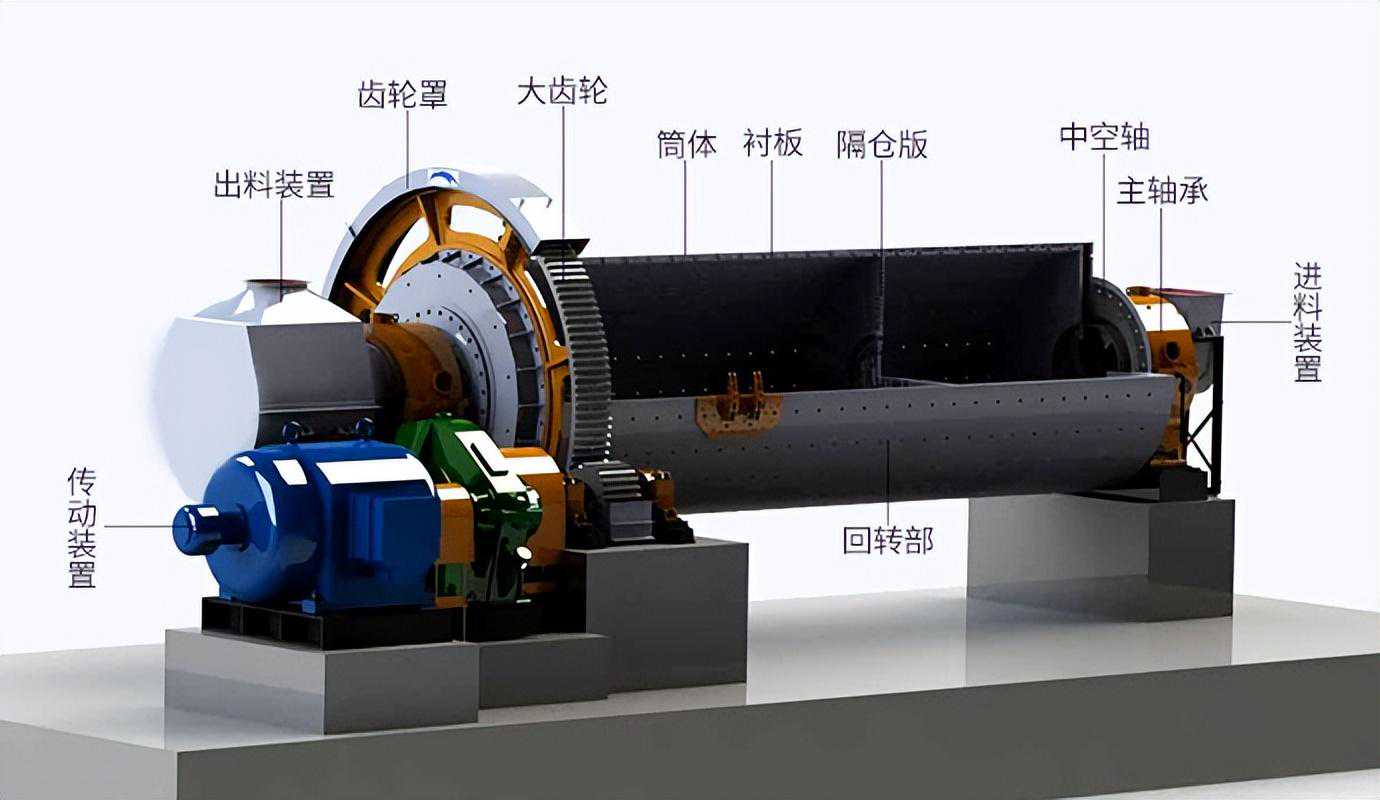人类的审美活动中,与声音关系最为密切的,当属音乐相关声景,而器乐声景当属音乐声景中最重要的内容。
古代器乐主要包括钟、鼓、琴、笛等各类乐器听觉声景相比于视觉图景,更具有穿透性。
恰如韦尔施在《重构美学》中所论:“我们有眼脸,没有耳睑。听的时候我们一无防护,听觉是最被动的一个感官,我们无以脱逃喧嚣吵闹。”
因此在生理本能上,人类无法对听觉回避。但是从心理、意识层面,人类可以通过声音的选择,内化心灵。
因此日常生活中,文人常会借器乐声修养身心,调节情绪。
人类对声景具有选择性,能在生活情境中诸多嘈杂声景中选择自己想要听见的声景。人类“只听到期待要听见的”。

又如心理学家Cherry于1953年提出的“鸡尾酒会”理论。
指出“在嘈杂的‘鸡尾酒会’环境中,当目标本身的一些特性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时,听者能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目标声景”。
因此,特定场域中的音乐能为听众,从嘈杂环境中提取,进而内化听者心灵。
小说中美妙的音乐,触发人们自觉听觉聚焦,使得勤政楼下的民众,在嘈杂无序的环境中,被音乐吸引,进而以达到“止喧”的目的。
音乐于此,起到了“以乐止喧”不仅内化人心,使人自发静听,也达到了维持秩序的目的。
由此可见,音乐对个人与社会均有巨大的文化意义,本节将重点探讨小说中“钟鼓声”“琴声”“笛声”对小说叙事与人物塑造的重要影响,并探寻其文化意义。

钟鼓声较之于人声,可以实现更大范围内的信息覆盖,也是权力传达的媒介载体。
“人类联系的建立,是从利用视觉符号演进为以听觉模式为主,最根本的因素是声景能让人可以在较远的距离沟通。”
因此钟鼓声作为重要的人籁声景,为人所利用,赋予其特殊的符号意义。是规范军队、维系社会规则、情礼法度的信号音。
洪亮、庄重的钟鼓声凭其广阔的穿透力,和不可逃避性,成为一种常见的制度型声景,承担着社会功能,制约着“共听”空间中的人。
古代小说中的钟鼓声基于其声景特征,具有权力与超凡两大特性,因而不仅可以制约行为,还能震荡人心。
因此小说中的钟鼓声重点围绕其与听者关系,不仅具有小说人物形象塑造,体现人物转变的功能,还能充当小说中分隔、串联叙事空间的标志,体现出社会秩序与混乱的冲突,进而引申出救赎情节,凸显出情与礼的冲突。

(一)具有权力属性的钟鼓声
自先秦以来,钟鼓声就作为一种制度型声景,充当军队进退的听觉指令,如《荀子·
议兵》所载:“闻鼓声而进,闻金声而退。”小说中也常有“鸣金收兵”“闻鼓前进”的情节描写。
钟鼓声景,传播广远且具有指令性,因而具有权力属性。这种独特的声景属性不仅为军队管理所利用,随着古代城市的发展,也为古代都城管理所利用。
唐代作为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,也是古代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。
因此唐代都市中钟、鼓楼同时出现。
钟鼓楼的并置使得钟鼓声逐渐成为唐代城市重要的声音景观。
钟鼓声不仅承担着唐代城市的报时功能,还影响着城门的开闭,影响着城市空间的变化。
《唐六典》中就记录着京师长安利用钟鼓音来控制城门启闭的制度,时原以金吾口传,人声传递。
直到太宗朝马周奏请设立“街鼓”制度所谓:“先是,京城诸街,每至晨暮,遣人传呼以警众,周遂奏诸街置鼓,每击以警众,令罢传呼,时人便之。”唐人特称为“街鼓”。

唐代实行严格的坊市制,基于此设立的城市街鼓制度,有晨昏报时的功能,规范了官员百姓的起居和出行。
暮鼓声起,全城实行夜禁,宫城、皇城、外郭城和坊里各门依次关闭,在夜禁时间内,禁止城市居民外出。
长安城民根据钟鼓声闻声而动,体现出声景对城市社会秩序的规范。
由此可见,响彻城市的唐代街鼓声,规范、分隔、影响着城市市民的生活,是表其权力属性的典型声景。
街鼓声作为一种时间标准而存在,城市居民的时间感和秩序感由此逐渐确立。
同时,作为一种制度性声景,街鼓声也象征着统治阶级对民众管理,彰显着社会秩序的权威性。
街鼓声作为古代城市地标式声景,逐渐成为古代市民生活的集体听觉记忆,成为都城的听觉符号。回响在古代小说中。

如小说《张直方》中,张直方日暮下的郊外环境书写中,就是以远方隐约间的城市街鼓声作为长安的隐喻。
街鼓的权力属性,还影响着小说叙事。
小说中的“街鼓声”高度写实,不仅贴合小说的史传传统,还作为一种故事发生的时间信号,提示小说时空,影响着小说情节的演进。
暮鼓声本来充当着小说情节中解禁与宵禁城市时空转换的标志。
城市街鼓声利用其不可逃避的听觉特性。象征着社会法礼秩序的公约性。
然而小说中郑生却“闻暮鼓不归”,听而不闻的郑生,破坏了社会法礼制度,并推演出郑生后续犯禁生活情节的展开。
标志着郑生形象从恪守礼法向情欲放纵的转变,从情欲禁忌向情欲解禁的转变,体现出个人情欲与社会礼法制度之间的矛盾。

(二)具有超凡特征的钟鼓声
在上古宗庙祭祀中,常以钟鼓作为重要的信号声,以指令仪式的进行。
如《诗经》“颂”的部分,那些宗庙祭祀为主的乐诗,多用鼓演奏。
从早期志怪小说开始,鼓声就作为一种制度型声景,具有超凡、通灵功能,震荡人物心灵。
超凡的鼓声。
可以同时存在于虚拟与现实空间中,沟联起虚实空间,常被作为提示阴阳转界的听觉符号。
早期志怪小说侧重于鼓声描写,而钟声则多出现于佛教相关志怪小说中。
随着佛寺数量的不断增加,佛教的戒律体系不断完备,使得古钟由象征皇权的政治礼乐之器,在佛教中成为弘扬佛教的法器。
寺庙中常用钟鼓来提示斋饭、讲经、集会、迎客等仪式,执行着“晨钟暮鼓”的宗教传统。
寺院钟声,庄严洪亮、却又深隐通灵的特征,与佛法教义相契,如佛经中有“若打钟时,一切恶道诸苦,并得止息”之论。

《行事钞上之一》中亦曰:“我鸣此钟者为召上方僧众,有得闻者,并皆云集,共同和利,又诸有恶趣受苦众生,令得停息。”可见本身在佛教中鸣钟就有解脱受苦众生之本意。
王梵志诗“闻钟身须侧,卧转莫前眠。万无常去,免至狱门边。”表达的即是此意。
寺院的晨钟暮鼓作为宗教仪轨的同时,还能渲染出浓厚的宗教氛围,唤起民众对彼岸世界的想象。
因此,钟声在小说中起着联通人世与幽冥空间的功能作用。
如《续高僧传》记载禅定寺僧人智兴寒夜中赤手敲钟,以钟声响彻地狱,钟声联通起人世、幽冥虚实两境。使得众多蒙冤受苦的鬼魂因声而脱冥、解厄。
张读《宣室志》中写窦某与刘溉在阴间相遇,窦闻刘诉“幽显之恨”,于是窦被令还阳,在冥途中闻,“击钟声极震响,因悸而寤”。
《宣室志》还记载娄师德为布衣时,梦中地府的按掾预言其未来能“出入台辅”。
上述小说中,寺院钟声同时存在于阴阳两界中,联通阴阳、是助凡人脱冥府转回阳间的工具,引导出冥的钟鼓声置于佛教寺院中,具有助人脱厄解厄之宗教义旨。

诚如有学者所言:“在钟与佛的融合中,诗获得了丰富的思想蕴涵,钟声带给人的不是政治象征的高贵尊严,而是超尘脱俗的阵阵清凉。”
特定场域下的钟鼓声,作为一种制度性声景存在,主要体现出超凡与权力两大属性,声景可以通过侵占空间来夺取听觉霸权,从而变成管理的工具。
因此,城市中的钟鼓声为统治者社会管理所应用,而在寺院中,受佛教文化的影响,钟声不仅具有报时之用,往往还能救冥之用,唤引民众的宗教向往。也是佛教世俗化的一种听觉手段。
透过古代小说中的描写,可以看出古代钟鼓声不仅禁约着民众,也感召着民众。